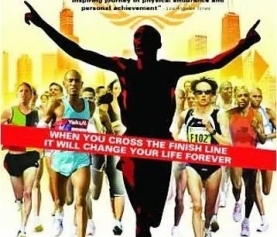甚嚣之处,必留有荒野(一)那些优秀的户外题材电影
早段时间被Jimmy Chin拍摄的以世界攀岩大神Alex Honnold以free solo攀爬酋长岩的纪录片《徒手攀岩》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这件事刷屏,整个世界的户外人都在众星捧月般的喝彩中忍不住想象:难道户外题材影片迎来了春天?
2014年,Alex Honnold与David Allfrey(左)在酋长岩速攀,大多数时候他还是会使用保护装备的。图片来源 instagram
那些优秀的户外题材电影1.jpg)
的确,一直以来,户外极限运动题材都被认为是拍给小众爱好者看的,大众看起来有门槛或者有距离感,甚至无法理解那样的生活方式。这部电影能在奥斯卡奖中脱颖而出,说明大众对户外题材的影片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关注。
户外题材的好电影很少,鲜有进院线上映的,纯粹的户外影片往往只能通过某些大型户外电影节才能集中观赏,如班夫山地电影节、欧洲户外电影巡展、肯道尔电影节等,攀岩类每年也有REEL ROCK(磐石电影节)可以看。
徒步类的电影就更稀罕了。登山探险题材的电影,如《绝命海拔》《垂直极限》等,常常讲述山难事故,生死攸关、惊心动魄,而徒步呢?缓慢的行走,能拍出什么花儿来?
其实,徒步这种慢节奏的题材也有其迷人之处,它代表着一类人的性格态度,一种格调,一条通往自己内心的探索途径。
那些优秀的户外题材电影2.jpg)
我们要推荐的这三部徒步电影——《涉足荒野Wild》《沙漠驼影Tracks》《林中漫步A Walk in the Woods》,不约而同都是长距离徒步且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来。不妨跟随这篇文章,寻着蜿蜒远去的道路,回味电影曾带给你的触动和思考。
那些优秀的户外题材电影3.jpg)
关于徒步的热爱与哲思
踏上道路,我们便有了一种使命感。不管道路的尽头等着我们的是什么,走在路上便是一件非凡的事情。
喜欢走路的人必能参透行走的乐趣,就像喜欢读纸质书的人必然爱着指尖与纸页的摩挲、爱着断行翻页时的目光流转。徒步的人爱着什么呢?爱着脚下并不平整的路,林间稀疏斑驳的倒影,日出日落与满天繁星,爱着沿途的休憩站和木屋,途中擦肩和相伴的行者,还有神秘难料的远方。
有人说,爱着徒步旅行中的自己。
那些优秀的户外题材电影4.jpg)
带上SCARPA Zodiac Plus,爱上徒步,享受每一步。
华兹华斯那声名远播的小短腿一旦来到路上,找准了方向就变得生龙活虎、健步如飞,他将自己的双腿当作哲思的工具。尼采也曾言明“只有那些来自徒步行走的思想才算有价值。”
人究竟是如何通过行走认识自己的?英国著名行走文学作家罗伯特·麦克法伦的看法是,“徒步旅行混合着旅行者的激动兴奋、力不从心、倦怠、奇遇和感悟……感受到的压力、摸得着的质地和看得见的空间能对人的肉体产生作用,也能对人的心灵产生作用,改变思想的纹理和倾向。”
那些优秀的户外题材电影5.jpg)
“能对人的心灵产生作用,改变思想的纹理和倾向。”通俗一点就是能想通很多事吧!
通过优秀的电影作品可见一斑,尤其是传记和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,这种半纪录半演绎性质的影片,真实度更高且更具有借鉴意义。以观影去探究某一类事物的共性,从人物角色身上找寻自己的影子,是这三部徒步题材影片得以出现在这里的原因。它们题材相同却蕴藏着三种不同的主题,分别代表了三种踏上长距离徒步的动机与期许。
第一部:涉足荒野——救赎
那些优秀的户外题材电影6.jpg)
那些优秀的户外题材电影7.jpg)
电影中的谢丽尔(上)以及现实中真实的谢丽尔(下)
那些优秀的户外题材电影9.jpg)
影片刻画出她毫无徒步经验的细节,例如穿了一双太小的徒步鞋,后来在山上滚落一只,赌气的她索性把另一只也扔了出去。(错误示范,请勿模仿)
那些优秀的户外题材电影10.jpg)
徒步太平洋山脊径,我们会建议谢丽尔选择SCARPA R-Evolution Plus GTX,中高帮保护脚踝,GTX防水透气,Vibram大底防滑,行走于雪泥混合的山路毫无压力。
那些优秀的户外题材电影11.jpg)
或者选择SCARPA Kailash Trek,轻盈灵活,为徒步减少负担。
道路具有治愈的功能,这一点,徒步旅行者并不难得出结论。
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·缪尔(John Muir, 1838.4.21~1914.12.24)曾经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徒步1600公里到达佛罗里达州最南端的岛屿,他认为“走出去,真正意义上是走进来”。
那些优秀的户外题材电影12.jpg)
约翰·缪尔,早期的环保运动领袖。
虽然我并不认为所有的心理问题、情绪问题都能通过徒步(或其他形式的旅行)得到治愈,也并非所有走在路上的人都有毛病,但这不失为一种无害的尝试。远离那些令你发狂、揪心、失眠、迷茫的人和事,踏上遥远、未知、全新、漫长的徒步旅行,让那些需要你独立去面对和处理的路途之中的问题占据你的身心,让每日不重复的风景充盈你的双眼,你会发现生活原来可以那样简单,日常所需的物资其实可以一个背包就装得下,原来这个世界除了你陷入的那片方寸之地还有如此辽阔天空……
其实,我们是被生活分心了,忘了曾经那么努力走来的初心是什么。
那些优秀的户外题材电影13.jpg)
你想要咆哮,却被现实扼制住喉咙。
谢丽尔·斯特雷德被她母亲的死分心了。
她对母亲的回忆,带着怜悯和追悔,那个从未尽过责任、不断向母亲施以暴力的父亲,是母亲前半生的痛苦来源,离开父亲之后,母子三人相依为命的平静生活却被突如其来的癌症所打破。母亲的离开让谢丽尔失去了人生支柱,“内心失去了一部分”,巨大的悲伤之下她做出一些非常出格的事情,例如背叛深爱她的丈夫、滥交、吸毒。
是什么样的痛苦让一个女孩堕落至此?不曾经历过的我们或许无法理解,先不要着急批判,回想自己,或许也在某些不理智的情况下做出一些荒谬的事,她和你一样想要分心,逃避不愿面对的事实。
“那些行为有悖于我的价值观,而且令我的痛苦更加不堪,那时的我经常会想,如果我死了,谁又在乎呢?”谢丽尔在她44岁那年的一次采访中说,“我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有些人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”
逃离的方式有很多种,幸好,谢丽尔选择了以险制险——用走进荒野的冒险去克制糜烂人生的危险,踏上太平洋山脊径寻找迷失的自己。
那些优秀的户外题材电影14.jpg)
能不能跟自己和解?能不能别难为自己?
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。现代徒步者兼作家最具影响力的是乔治·博罗(George Borrow,1803.7.5~1881.7.26),他掀起了那股席卷19世纪中期欧美大陆的探寻道路和对小径充满浪漫向往的浪潮。
但博罗其实是抑郁症患者,自小就有一种被他所称的“恐惧感”所笼罩,唯独“步行是他摆脱忧伤的一种方式。”他走遍了英国本土的每一个角落,又穿过海峡走进法国、西班牙、葡萄牙和俄罗斯,向南直至摩洛哥。在这成千上万公里的徒步之中,他概括出了广为人知的徒步旅行者箴言:
有白天,有黑夜,太阳、月亮和星星,这些都是好东西。
同样还有荒野的狂风。
生活是非常甜美的,兄弟。
谁还想死呢?
那些优秀的户外题材电影16.jpg)
乔治·博罗的徒步旅行者箴言
是啊,谁还想死呢?
当谢丽尔结束长达94天4200公里的徒步、通径走完太平洋山脊径时,她肯定不会想死;当她和当时那条路上唯二的女性徒步者坐在夕阳下聊人生的时候,一定没有在想死;当她咆哮着“F**k”把剩下的一只鞋扔进山谷时,顺便把她积压已久的怨恨、愤怒、痛苦、愧疚统统都发泄出来,那一刻来不及想着死;当发音乐会传单的迷人男子出现在她面前时,应该也没空想着死。
那些优秀的户外题材电影17.jpg)
你看,徒步就是有这样的魔力,让你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,但又不能不当回事儿,最终在“在乎”与“不在乎”之间取得平衡。那些该死的烦恼,或许等到你走得肉体通透,就变得不再重要。
未完待续,请看下一部《沙漠驼影 Tracks》